Connotation, Dilemma and Approac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
-
摘要:目的/意义 我国乡村振兴是要通过新时代的创造变革,实现从离乡背井到以德法治乡的集体经济的全链重建。方法/过程 通过文献研究和分析归纳,研究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解,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与疏离,探讨约束乡村振兴的不利环境和制度缺位等因素,提出乡村振兴的举措和优化路径。结果/结论 人们对于乡村牧歌的精神自由成为无数有志者终生的理想,这也成为乡村始终具有吸引力的基础。为了创造可以回得去的乡村,需要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让乡村真正成为安放乡愁的温暖家园。Abstract:Objective/Mean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s to realize the whole-chain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leaving their homes to the rule of virtue and law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reform of the new era.Methods/Procedure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alysis and summary, the opposi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re studied, as well as the impact and alienation of urbanization on the rural culture, and then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absence that restricte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discussed. Last, the measur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put forward.Results/Conclusions People’s spiritual freedom for rural pastoral songs has become the lifelong ideal of countless aspirants, which has also become the basis for the attraction of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countryside that could be returned to,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were needed to make the countryside truly become a warm home for settling the nostalgia.
-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从离乡背井到以德法治乡来一场以人为核心的全链体系重构,这种重构以人为本、以法为根、以德为要,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复振的趋势。中华文明是按照天地阴阳构建的天道文明,而乡村是这种文明的源头,蕴含着“从何而来,要去哪里”的终极秘密,正是从这里开始,华夏文明最原始的基因图谱得以绘制,五千年的文化自信被镌刻在中华大地的柱石上,荣辱兴衰,沧桑巨变,岁月与朝代更替,华夏文明却生生不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近乎到了日趋凋敝的状态之中,人口流失、土地荒种、技艺断承[1]。一方面是大批人到了城市中发展创业,守成兴业,异乡漂泊;另一方面却是乡村文化凋敝,人口凋零,经济破败。有人将这种矛盾状态描述为“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人与自然的疏离加剧了人与社会的对立,在这种疏离了自然又缺乏社会归属感的道德秩序中,嫉妒、焦躁和孤单感不断滋生[2],道德心理上的困境使人变得功利而又冷漠,心灵变得空虚。
1. 人与乡村的和解与融通
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感性的表达。人与自然之间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来表达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3]。自然给予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与改造自然,通过这种价值交互的方式,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并紧密结合起来。两者的紧密依存形成了一种自然法则,人与自然的和解成为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违反了这条法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会被打破,自然界的报复就会接踵而来[4]。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数十年的野蛮扩张,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工业酸雨、植被破坏、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严重。
今日中国之乡村,多数地方看得到的是老人、留守儿童和看家护院的狗。乡村失去了青壮年就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只剩下一座座破败的房屋静静地守候着,活像一座座伫立在那里衰败的古堡。老人和孩童坐在门口等天黑天明,等村头汽车的轰鸣声。这里的人生命不再起舞,阳光灿烂却又多得不知如何使用。留在乡村的人也是那些远离家乡者的牵挂,只是电话响起,不知道如何倾诉情感,草草几句,就挂线收场。房子就是那么奇怪,只要有人住着,不管多邋遢,总是用力地焕发着生机,而一旦没有人常住,屋子和院子的破落总是挡不住。时间久了就成了昆虫杂草的福地,这种萧瑟也更使得房屋的主人没有了再回来居住的念头,久而久之,自然和时间共同淘汰了异乡人归乡的居所,催生了更多的异乡人。
乡村是静夜童年的梦境,亦是长大后念念不忘的根。那些在心绪上徘徊于家乡与他乡的游子,像是游荡在时光之海上的旅客,既有对家乡的牵念,亦有奔赴星辰大海的使命与担当。乡愁的背后,是童年的记忆、是叶落归根的传承,找不到乡土与现代文明和解的方法,就无法排解这种愁绪。在无常的历史变迁中,在自然或人为的灾难中,乡村的文明、乡村的风俗、乡村的发展,无不在发生着令人叹惋的变化,这种变化莫非就是乡土社会的最终命运?人与乡村情感的割裂,如何化解?人与乡村的发展如何融通?幸运的是,乡土的传统、乡土的思维、乡土的文化在中国如万古江河,虽然可能会改道,但是从来不会断流。而中国乡村振兴的文化重建也需要在这里寻找答案。
2. 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城乡分离
西方的工业化是一条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之路,但也走向了极端,走了很多弯路。粗暴的机器生产方式使得大批的百姓失去土地,进入工厂,人和自然被隔离,地方性的意识和归属被打破,人回不到自己长期生活并依赖的土地,又未能及时适应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冲击,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解、融通和互惠被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失去了真实的交流,自然也失去了循环,劳动被异化,信仰不断逝去,社会化问题不断凸显。传统的原始村落文明被瓦解,新的文明没有完全形成,贪婪成为社会的常态,丑陋而又粗暴的治理让更多的人对整个社会的认同和归属缺失。自私、懒惰、劫掠、毒品和传染病,这些成为社会问题的常态。曾经有观察家这样评价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场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给英国人带去了灾难,尽管它带来了科技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但是它加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精神信仰危机。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发展阶段、不稳定发展阶段、停滞发展阶段及改革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改革后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共同推进的[5]。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分工与专业化使得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活动大量聚集在城市,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密集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发展特征逐渐显现[6]。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城市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福利与农村不断拉开差距,更多的农民工不断涌向城市。而他们生产技能偏弱,基本生活条件、生产安全、劳动报酬保障措施不力,工作和生活权益容易被忽视,工作方式、工作条件及工作权益的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民工容易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新贫困者。
在这种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中,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改变了国民工作的家庭模式。在城镇化之前,很多家庭是一人上班养活全家,现在的城镇化发展增加了家庭生活的成本,多数家庭需要夫妻两个人都出来工作,有了孩子以后如何平衡工作和照看孩子成了家庭的一个重要矛盾。即使解决了孩子照看问题,女性在这次工业和城镇化发展中可以寻求到更多工作的机会,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实现了经济独立的女性全职处理家庭事务的意愿就会下降,女性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已经形成,但是不少男性还没能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认知中纠正过来,大量单身青年群体出现,离婚率不断上升,使得无论男女都不切实际地寻找更“理想”的伴侣,加上生存、教育、医疗等多重因素的合力,少子化问题也愈发严重。
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治理过程中,选择绝对的“城市一元”模式还是“城乡二元”治理没有经过太多波折,“二元分治”还是“城乡二元融合”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拉锯。部分城市对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后政府职能调整的认识不足,长期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治理思路、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7],出现了规划体系不完善、规划机制不科学、规划执行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城乡户籍制度成为政府控制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成了城市和乡村之间一条巨大的鸿沟,自由流动的天性被抑制,农村与城市的双向流通被阻隔,求稳怕变、不愿冒险的惰性心理不断滋生,两者间的居民对彼此的认同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抑制限制了城市化发展,工农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错位,社会资源的整合度下降,催生了劳动力过剩和资源相对紧缺同时出现的奇怪现象。
3. 乡村文化与工业文明冲突后的疏离
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乡民们有着共同的地域和生活空间,形成了休戚与共的生活情感,价值观和信仰融合生长,最终会形成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和乡缘亲情的乡村文化共同信仰,形成“共同体”。在这种看似无形,却又结合紧密的乡村共同体中,血缘、地缘和伦理是主要的链接要素,宗族、邻里和乡亲是交往的主要对象,共同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依赖形成了彼此守望、亲密无间的乡村社会交往模式,形成了一种亲密的、纯粹的、隐秘的共同生活。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升,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日趋扩大,以“有机团结”为代表的商业化城市成为社会的代表,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乡村共同体”不断受到冲击而被割裂、疏离。“村落共同体”经历着社会细胞的裂变、消亡和新生,乡土文化体系和人际关系随之嬗变[8]。“乡村共同体”和“宗族共同体”对成员的影响不断被弱化,成员变得功利且急迫,精神皈依的途径被切断,成员普遍陷入了迷茫和焦虑。这种变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维系乡村基层顺序的“序”丢失了,传统道德被碎片化,道德约束力的下降使得乡村居民的“越轨”行为日趋增多,这种变化至少在三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3.1 乡村治理的基础开始形成缺位
过去,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乡贤的荐举是基于乡民之间长久地信任和了解。现在的乡村选举容易受资源、财富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监督和管理上也存在一定的缺位,容易造成村庄强势者上位、恶势力霸权等现象,从而造成乡村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的不公,造成乡村贫富差距过大和村民大量外出后的进一步萧条和落败。
3.2 人才和资源稀缺进一步拉开乡村贫富差距
真正有眼界有能力的人才在乡村中分布不均。经济好的乡村中人才集中,而监管体系在乡村的专业性和覆盖程度尚未能满足需要,容易形成能人、强人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挤占乡村集体资源,霸占乡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通道。而在经济欠发达地方的乡村中,人才的缺失又会影响村庄集体协调能力,造成集体行动能力的低下,从而进一步和富裕乡村拉开差距。
3.3 乡村文化信仰不断衰败
受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影响,乡村文化信仰不断衰败。错误的价值观和扭曲的消费观不断侵蚀乡村居民,传统乡村结构遭到破坏,地缘、血缘观念被不断弱化,信仰链条被不断切削。从过去的乡村文化信仰到后来的姻亲和利益关联体纽带,乡村传统文化沦丧,利益至上被不断放大,农民的被妖魔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剧的。
4. 城市和乡村文化体系的重连
西方国家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上采用直接的方式,即直接以城市的一元代替城乡二元,这种好处就是建立很多绝对的城市文化中心群,缺点就是伴随着乡村的衰落和消亡。中国具有近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不允许采用这种绝对的一元制,“城乡互构、二元融合”成为必要的选择。这种结构下,没有绝对的中心,也不存在绝对的边界,城市和乡村相互依存、双向流通。过去乡村共同体的发展研究,更多是从乡村经济的视角去切入,现在拓展视角后,将村落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交互关系以及家族的变迁、村落文化的发展、乡村环境的变化和区域特色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注入了活力,适应了新的发展形势。
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建设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实现价值生态的聚合。需要从乡村发展的全链条上实现振兴,打造具有时代特点,适应城乡经济融通的集体经济,实现乡村经济活力的恢复。这种生态体系是建立在产业兴旺基础上的,而在这个全链条重建中,人是核心资源,不但要有年轻人,还要有具备知识与眼界的高素质人才。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回家,在过去乡村讲究的是成为乡贤乡绅,功成名就后落叶归根,捐资助学、兴学兴教、兴修祠堂,然后再把年轻人送进城市,为国家举荐人才、培育栋梁。一代又一代,村里生长,城市贡献,然后再落叶归根,长此以往形成一个闭环的人才成长、培育和输送中心。今天乡村文化的没落,宗族制度的消失,乡村文明的消沉使得很难形成过去那种人才输送模式。但是这不妨碍从新的形式上出发重新构建一个乡村振兴的体系,毕竟人才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轨迹没有改变,乡愁和乡恋还是不少城市打拼者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乡村未来可以定义为精神资源供给领地。有了人才的双向流动,就有了乡村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人可以驱动人,土地、资本、资源、文化、科技等要素才能交汇创新。而人与乡村的情感割裂是长期发展的诸多因素造成的,打破这种割裂首先应该是人与乡村文化上的认同和回归,促使人与乡村之间从若即若离到和解互惠。
乡土情怀的文化寄托中,乡语是最直接最生动的音符,少小离家,乡音无改是游子的常态。方言是特定区域内的语言变体,是地方文化交通最便捷的桥梁,语言空隙下的心灵隔阂才是离家愁绪滋生的主因。在乡语的语境中,蕴含着一种平衡的力量,能够将具有文化创造力的人与作为有着某种自我去文化倾向的自然之间做平衡和互依。失去乡语不必然失去这种平衡,但是部分失去这种平衡的后果是严重的,不论是纯粹的文化化,或者是彻底的自然化,心理约束规则被打破后,人就像一个强大却又失去社会法则约束后进入茂密丛林的巨人,恣意践踏却又不断地伤痕累累。人和自然之间相互被隔离开来,看着身边触手可及的树木森林,却又被禁锢着无法突破的重重藩篱,撕扯不掉、挣扎不开,久而久之,伸手触碰外部世界的意愿就小了,人和自然相互疏远,最后的结果就会日趋走向一种荒野化,陷在失语与异语后的苦闷里。异语背后群体之间的心灵距离不是靠走近就能消融的,需要回到时空的原点,距离才会消失,又抑或是熟悉的乡语驱散久离无归的愁绪。失语现象象征着文化的消融与重构,失语现象隐含乡村意识消退所带来的恐惧,乡语中蕴含的文化眷恋与文化归宿是能够给那些离家万里不能归来者最好的慰藉,能够用乡语呼唤游子的声音、作品和场景都是温暖的。
乡土文明塑造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可以相互认同、转化和依存的家园意识,这种意识使得土地和财富可以流转,宗族血脉可以传承[9]。信仰不息使人可以借由自然的存在而成就自己的存在和不朽,这种信仰的传承成为乡村最基础朴实的乡村文化。衣锦后还乡,落叶后归根。这是乡土对游子的呼唤。而魂归故里,入土为安则是对乡村成长者灵魂最好的安排,成为人克服死亡恐惧的力量来源。这种信仰力量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经过成百上千年的传承,早已成为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管社会如何变迁,外部压力如何强大,他们对于这种信仰和追求的动力从未减少。有了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功能属性,这种信仰的文化就有了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很多农民会将这种信仰赋予神圣与灵验,他们不认为这种灵验是一种超验或神秘的存在,而是最为具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的诉求和表达。有了这种功利性的诉求,对于土地的崇敬就有了地位异乎寻常的神圣性,人们愿意为之贡献几乎全部的信任。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村落可以拆除,宗族寺庙与祠堂却必须妥善安置,这是农民对于土地和乡村文化最后的守护。
5. 现代乡村文化的转型和重建
人劳作于土地,留恋于田园,守护乡村如守护自己的心灵一般,以自在的种种作为去抗拒繁华社会带来的种种不安和侵蚀。生活的节奏成了生活与自然共同谱写的规律,劳作的人不断受到文化浸染,实现了对自然和生活的合拍和融入,获得了生命所渴求的安全感。人们学会合理地利用自然,融入自然。自然又毫无保留不断供给与再生,循环往复。生活的日常变成了惯习,惯习又因了地方的形塑成了符号和韵律,文化得以形成,归属和认同在这里交汇,人与自然之间交融,良性循环得以实现,被这种乡村文化气息和韵味浸润过的人,有根、有魂、有力。能走很远,也懂得回家的路,这些便是一个乡土文明最为根基性的保障和连接,不管是否看得见,但是集结的力量永生不灭,像一株株庞大根系的融入,牵动着远方的游子。这是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文脉络,抓住了这个软核心,再难的事情都有了核心的支撑。所以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中,对乡村文化的重建应有此认识[10]。
从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发展是时代趋势,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传统村落的衰落难以避免。但是道德失范、发展失序不是乡村独有的社会问题,看待这种社会撕裂需要科学的认知和方法,而不能是走返璞归真的“回头路”。对于“农耕文明、淳朴生活、乡土价值”这些传统的乡土文化元素,很多人潜意识里是不认可的,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对这种生活的不认同甚至是一度将其打上“落后”的标签。现代化城市生活也存在缺乏归属和缺乏价值认同等各种问题。中华民族能够得以生生不息,依靠的是华夏文明数千年的薪火相传,而从农耕文明走过来的乡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从黄河岸边走来的先辈们,血脉里流淌着黄河桀骜不羁的力量,也透露着黄土地朴实无华的气息。虽然乡村文化已经衰败,但是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符号却四处可见。乡村文化的振兴需要尊重乡村传统价值和历史地位,扎根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挖掘精华融入时代创新元素,重构乡村价值体系,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使之扎根广阔乡村,焕发时代生机。
6. 创造回得去的乡村
人在生存需求满足后,基于对生活过的土地的认同和依恋,往往会有一种归乡的渴望和挂念。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人们出则居庙堂之上,归来则是乡村牧歌。这种精神的自由成为无数有志者终生的理想,这也成为乡村始终具有吸引力的基础。乡村成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幸福生活所奋斗的动力来源。虽然今天的科技发展阻隔了这种情感联系,却始终无法隔断人们渴望回归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的期盼。游子需要回得去的乡村,而乡村的振兴也需要回得来的游子。
6.1 回得去的乡村需要制度创新
如何让年轻人从城市回流,让家乡吸引技术人才和年轻劳动力需要制度创新。人才引进制度需要完善,人才优惠补贴需要落实,乡村创业环境需要改善。而实现政府权力有效合作和农户利益置换,同时又不打破现有政府权力边界和农户利益结构就更需要创新。乡村建设和管理需要制度支撑和保障,需要管理者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
6.2 回得去的乡村需要技术创新
科技兴农就是要给乡村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将先进理念、智慧技术、现代装备引入到乡村农业发展,“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随着数字生态技术在农业的广泛应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了强大动力,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被深刻改变,这也为乡村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多机遇。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坚持科技引领,坚持技术创新,充分激活乡村生产要素,激发农村发展内驱力。充分用好智能管理、数字生态技能优势,不断探索先进技术与农业发展的融合路径,助力乡村生态农业腾飞。
6.3 回得去的乡村需要文化创新
振兴后的乡村应该更像乡村,不但要有城市生活中的便捷,还应该具有显著区别城镇的乡村宜居风貌和生态环境。让归来的游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综合培育乡村的文化归源、文化认同、生态永续[11]。通过扶持乡村文化传播企业,培养新时代的乡绅乡贤。通过文化立乡来推动乡村特色生活、现代生活、绿色生活和乐活生活的有机结合,构建乡村文化的新生活模式,让乡村文化成为安放乡愁的温暖家园[12]。
-
[1] 赵旭东. 乡村何以振兴?−自然与文化对立与交互作用的维度[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29−37. [2] 张彭松. 人与自然的疏离−生态伦理的道德心理探析[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4(4):453−459. [3] 徐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学建构[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4):23−29. [4] 孔祥利. 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力内涵的生态诠释与双赢策略[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2−28. [5] 王金胜. 世界城镇化发展模式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30(4):118−123. doi: 10.3969/j.issn.2095-1361.2014.04.017 [6] 边晓晨,曹敏. 建国以来陕西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探析[J]. 价值工程,2012,31(27):303−305. doi: 10.3969/j.issn.1006-4311.2012.27.142 [7] 雷寒冰,陈晓卫. 我国城镇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 学理论,2013(35):51−52. doi: 10.3969/j.issn.1002-2589.2013.35.025 [8] 陆林,冯建蓉. 转型时期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与重建[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10):57−61. [9] 齐骥. “两山”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实现及文化启示[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45−155. doi: 10.3969/j.issn.1001-9839.2019.05.014 [10] 江仕敏. 以文化兴盛激活乡村振兴之魂[J]. 创造,2019(4):15−20. [11] 孙万心. 乡村振兴 文化发力−浅谈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恩施乡村文化创新[J]. 民族大家庭,2018(3):43−45. doi: 10.3969/j.issn.1005-1953.2018.03.023 [12] 李明. 职业教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支撑研究[J]. 现代商业,2018(16):160−161. doi: 10.3969/j.issn.1673-5889.2018.16.084 -
期刊类型引用(0)
其他类型引用(3)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234
- HTML全文浏览量: 108
- PDF下载量: 10
- 被引次数: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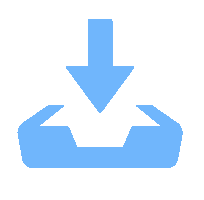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