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Objective/Mean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uzhou City, the green spac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the urban problems have emerged endlessly. In order to better alleviate the urban problems and maintain the health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landscape pattern of green space in Fuzhou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evolution.
Methods/Procedures By taking the green space in Fu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land use in Fuzhou in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GIS software. On this basis,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Fragstats software,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SPSS software.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uzhou City from 2005 to 2020 has resulted in a large decrease in the area of green space, among which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was the fastest and the largest, with a decrease of 95.38 km2. (2) The forest space, as the dominant landscape in Fuzhou, was reduced by 71.94 km2 in 15 years. Most of the reduced green space was conver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land, which increased the construction land by 227.87 km2, and the increase rate changed from rapid to slow to rapid. If the construction land continued to increase immoderately,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urban biological species would be affected. (3) It was found that the human factors such as per capita incom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urbanization rate and GDP were the key driving factors of landscape pattern change in Fuzhou. (4) In the future, the green spatial pattern of Fuzhou could be optimized by optimizing the habita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landscape patch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corrid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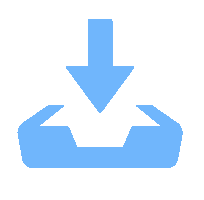 下载:
下载: